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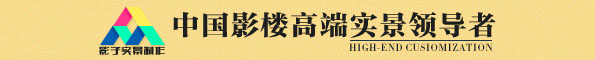
作者:杨跃飞
我承认我身上是有黄土标记的,即便自己生命中一大半的时光是在外地度过,即便早已在北京安家多年,现在依然习惯不了吃大米饭,每天恨不得一天三顿都要吃面食。
我出生在平原的黄土地上,在平原,没有一片树叶是干净的。那是风的缘故。平原上的风并不烈,只是一个字:透。当风从“西伯利亚”穿过崇山峻岭,经过了艰难险阻到达平原的时候,它一定是十分的惊讶,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地方呢?一马平川,任尔驰骋。
风到了这种时候,是不是也觉得有些累了,该歇歇了?它就像是从远方射出的一粒子弹,初时烈,距离越远质量越重,那些有质量的细小尘埃就此飘落在了平原的树上。在这里,风对树的侵害是无声的,它很少有刮倒树的时候。但它常年一次又一次地去侵袭这里的树,那结果又会怎样呢?
在平原的乡村,能给人以庇护的,除了房屋,就是树了。树的种类很多,数起来最原始的怕至少也有二十几种,以榆、桑、槐、楝、桐、椿、柳、柿、桃等.为主要树种。这里一马平川,雨水丰沛,四季分明,按说应是最适宜植物生长的地方。可坦白地说,这里不长栋梁之材。

在平原,树与风的搏斗是长年的、持久的,也是命对命的,就像是一对老冤家。如果你尝一尝树的汁液, 你就会发现,那是苦涩的。若是果树,或是汁液偏甜些的树,如果不打药,那肯定是要被虫蚀的。平原上的树有一个最可怕的,也是不易被人察觉的共性,那就是离开土地之后就变形了,这就是风对平原的树的影响。
这里常刮的风是西北风,西北风冬哨秋尘,且钻旋凌厉。所以这里生长的树没有特别直的,二般都是偏东南的朝向。如果你看见路边的树朝着东南歪一点,就像是在给人点头,那么,就离家乡不远了。
而这里的风对人的影响,刻在脸上,那就是岁月,而岁月一旦定了格,那就是风俗了。风俗是一个地域特定的生活习惯。老家的人是主吃面食的:面条、面饼、面汤、菜面窝窝等。吃面食须臾离不开的就是辣椒,辣椒是大家最重要的生活调味品。在庸常的日子里,没有辣子是吃不下饭的,辣椒吃多了,脸上就会生出粉刺来,如果在路上你碰上一个年轻人,一边走一边抠脸上的粉刺儿疙瘩,没错,那肯定是我的老乡了。
血脉的联系是必须要说的。不管走多远,我都得承认,我是那片黄土地的人。哪怕你一天也没回去过, 你的祖籍仍然是黄土地上的杨圪塔村。可我们杨姓这一脉从根上说,又不能算是地道的平原人。据说,杨家是从明代才从山西洪洞县迁徒过来的,但纸上的记忆是靠不住的。我对这片黄土地的记忆是儿时和村头的一个个老人“喷空儿”(在中原表示闲谈的意思)中深植入下来的。
村里有一座关帝庙,相传有500多年的历史。庙前有一座古塔,后年久失修倒塌,仅留有塔基,村民习惯称塔基为疙塔,后杨姓迁此建村取名杨圪塔,村子有2268人的大村子,村子地理特殊,东西南三面环深沟,北面是山坡,地少人多,也是本市最大的贫困村之一。
一条颍河蜿蜒穿过中原大地,颍河边上多有一望无际的芦苇荡,许多村子以编席为生,据说,他们编的席子一九五八年曾获得过巴拿马世界博览会金奖。
我们老家的村子就紧靠颍河,在村子南边穿过,两岸都是茂密的芦苇荡,听老人们讲,以前这里家家户户以编席为生。

过去,这里的男人普遍比女人低,那是背湿苇捆背出来的,这里的女人普遍比男人高,那是她们站在碾篾子的石磙上一脚一脚练出来的。
一到每年的八九月份,芦苇就成熟了,那时候,一大早,村子的女人们照例会让男人背出捆一捆头天晚上破好的蔑子来,由她们站在石磙上把编席用的篾子碾平,然后再去编。在村街上, 女人们一个个站在圆圆的石磙上,头高高地昂着,靠着脚尖的力量, 双腿的灵活,驱动着石磙在她们的脚尖下忽东忽西、来来回回地滚动。她们一个个脚法矫健,身子灵巧,就像是技艺高超的芭耆舞演员。这在村子里曾经是一道风景。
那时候人们生活贫困,吃饭是天大的事情,可一年四季总也不缺吃的,现在人们都讲绿色食品,可当年村子吃的全都是绿色食品。那时候人们吃过火烧的蚂蚱,半生不熟的嫩玉米,春天的槐花、榆钱儿、桐花,秋天的高粱杆,掺有棉籽的窝窝头,一股酒糟味 (窖坏了)的红薯,一碗一碗的水煮胡萝卜,九蒸九晒用盐腌出来的蓖麻叶,还有从老鼠洞里掏出来的豌豆。可以说,只要能吃的都被人们想到给填肚子了。
最让村里老人们不能忘怀的是三大美味。第一大美味是柿糠沙,也叫“炒星星”。那是晒了一冬的柿子皮加豌豆面、红薯干面再加辣椒面等用水和成面团,经发酵后拍成一个个圆面饼在阳光下暴晒,再经手工小拐石磨磨成粉状,最后在烧红的热锅里至少浇半碗猪油爆炒,这就炒成了晶亮亮的、看上去一粒一粒的油沙。吃的时候先甜你一下、再辣你一下,你得一点一点吃,辣得你长伸着脖子,满口生火,一腔红甜。我小时候没有吃过,但是看老人们陶醉其中的描述着,感觉肯定是人间美味。
第二大美味,是春天的时候,榆钱和槐花,这是小孩子的零食,也是村民餐桌上的一道主食,女人们把榆钱、槐花用杂面揉到一块蒸熟,或炒或凉拌。我在小时候,一到槐花和榆钱盛开的时候,就和小伙伴们比赛爬树,去够这些天然的零食吃,经常把两条裤腿磨烂,少不了被发现后的母亲训斥一通。
第三大美味是井拔凉水蒜泥薄荷叶蒜面条。女人们拿擀面杖擀出薄薄的面片,再用刀横切除细细的面条,抓一把地头野生的玉米菜,井水过凉,浇上蒜泥薄荷叶调制的料汁,大夏天吃上一碗,一天劳动的疲劳都赶走了。即便到现在,我在北京的家里也没事自己做,只是用的超市里买的挂面,也吃不到地头野生的玉米菜了。

待到收完芦苇,河边就搭起了一个一个过红薯粉的架子,下面是沉淀红薯粉的大池子,村子北坡上种的红薯过出的红薯粉质量最好,可村民们都不舍得吃,把最好的红薯过出红薯粉,然后把红薯粉卖掉换钱,把不好的红薯留着自己吃。一到冬天的时候,河边就一个挨着一个的过红薯粉的架子,夫妻两口齐上阵,小孩子就在河边自己玩,大冷的天里河边同样热闹。
冬天里能吃的东西不多,但是能吃的东西都可以通过火烤来吃,我小时候体弱多病,父亲曾经多次把从我家玉米秆堆里逮到的刺猬烤给我吃,拿泥巴把刺猬裹成泥球,扔到火堆里,再扔上几块红薯,等火熄灭了,红薯和刺猬肉都熟了,晚饭也就都有了。
冬天里有火堆的地方,就是一场大聚会,火堆越大人越多,冬日里闲着没事的女人们就围着一个大火堆烤火“喷空儿”,村里汉子们喝了酒就玩“顶牛”,一对一、头顶头,看谁把谁顶败了。小孩子们就围着一个老人,听老人讲村子里以前发生的故事,那时候没有电视,没有手机,会讲故事的老人就有许多“粉丝”。
对于小孩子来说,炉子边上的粉条、花生、豆子、粉条等等都能烤,只要烤熟就能吃,老人们说,他们小时候经常做泥蛋子红薯麻雀,也叫“双味麻雀”。就是把生红薯掏一孔,麻雀在盐水里泡泡,尔后塞进红薯里用泥糊了,放在烟炕房里的火道去烤,等泥蛋烤裂的时候就可以吃了,先苦后甜再咸,哎呀,所到这里老人砸吧一下嘴巴,好像又吃到了他记忆中的美味。
正是这些绿色食品丰富了我的胃,使我能在村子里茁壮成长。以至于后来,我一看到辣椒就浑身燥热,满口生火。辣椒是村子里最常用的一种佐料,是高挂在盐之上的一-种生活必需品,正是这种佐料诗意地毒化了我的童年。
当然,这是低层面的吃,如果要求再高一点,如果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,炒上两个菜,那就是吃酒了。现在有人说酒是文化,也就是“辣”的文化,是让人兴奋的文化,“文化”到了极点,也就是一个字:醉。让客人喝醉,这是村子里待客的最高境界。如果哪家来的客人喝醉了,醉成了一摊泥,那是待客的种荣耀。往往这时候要拉到架子车上,绕村一周,这是多么体面的事情啊!
村子里还有已给风俗叫:领席。在这里“席” 是要“领”的,想一想这有多么优雅。村子以前靠编席为生,最不缺的就是席子。那时候,一张席就是一张流动的床。村子里最重要、最私密的活动都是在“席”上进行的(一为酒席,二为炕席)。特别是到了夏天,主家领着一张席,客人或朋友相跟着,有瓜的时候,就去瓜地,或者是树下、河边、场院,带着盛了烟丝的笸箩、一瓶小酒、几根脆瓜、一筐花生,席地而坐,对月而谈。至于说些什么,那就不知道了。
那时候一到夏日的傍晚,人人都会领着一张席到处走,说是纳凉,可睡到半夜,忽然下雨了或是刮风的时候,就又拉着席走了,也许是去了炕房,也许是钻了麦秸垛,谁也不知道他或她到哪里去了。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那芦苇荡连绵百里,一眼望不到边,好像一生一世也割不完、走不出的样子,可是现在几十年过去了,整个芦苇荡早已经都消失了,颍河两岸也很少能见到芦苇荡了。
2018年,村子入选河南省第二批乡村旅游特色村,给留守在这里的村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,村民们现在也有了新的生活方式,不再为吃喝发愁,很多人都外出打拼更好的生活,村子里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外出打工,留下了老人和孩子在村子里留守,也有举家搬迁入城里生活再也不回来的。
现在走在村子的街头上,已经很少能遇到年轻人了,只有到了村里小学放学的时候,孩子们在村里叽叽喳喳的玩闹声,才让村子里有了一点生机。
一个老人蹲在街边的一个大石头上独自在抽着烟,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小孩子愿意围着他听听村子里以前的故事。

本站部分内容、观点、图片、文字、视频来自网络,仅供大家学习和交流,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。如果本站有涉及侵犯您的版权、著作权、肖像权的内容,请联系我们(qq:748492175),我们会立即审核并处理。